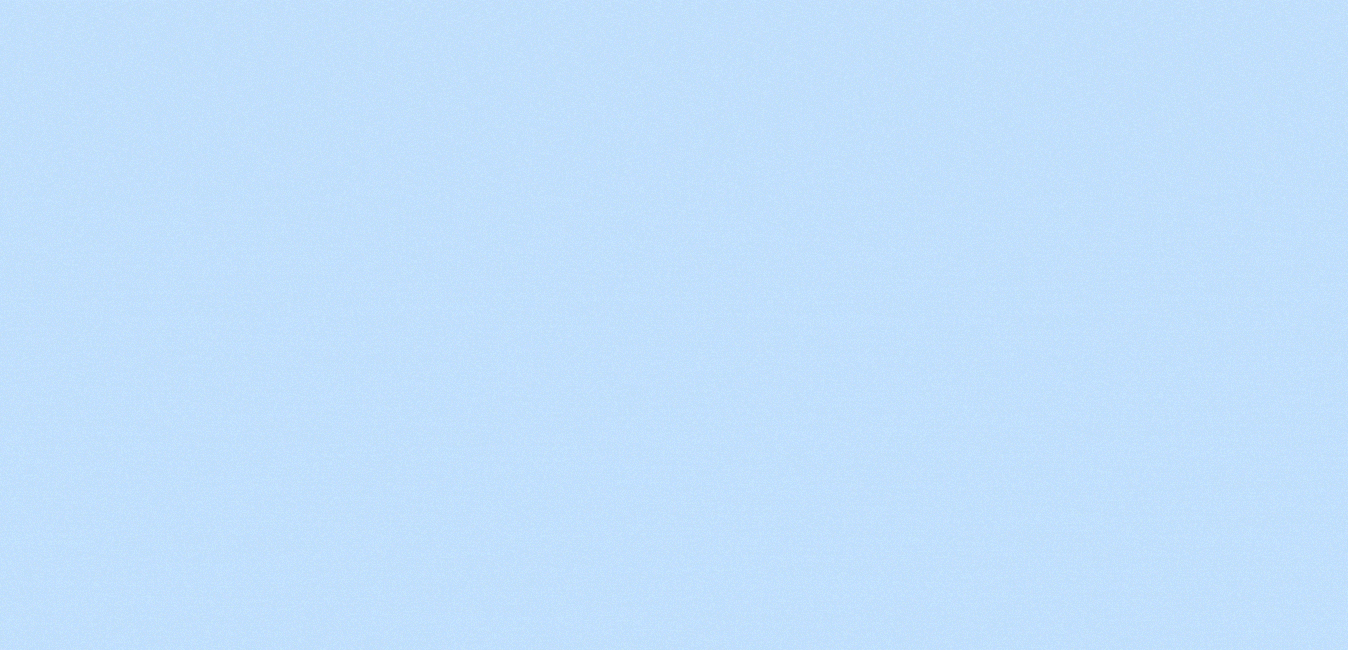曹雪芹故居“死而复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9.12总第106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84岁的张书才站在烈日下,见证眼前这个崭新的四合院的落成仪式。随着牌匾上的红布被揭开,“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几个大字正式亮相。这天是2022年7月29日。40年前,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地方,曹雪芹唯一有证可考的旧居就此浮出水面。
不过,他当年找到的曹氏旧居离这个新院子其实还有100米远,位于现在崇文门外大街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十字路口上。20多年前,为了修建两广路,在有关部门承诺复建旧居的前提下,那个旧居的院子被拆除了。没人想得到,后来,复建之路却跌跌撞撞走了20多年。
与曹雪芹后世的巨大名声相比,有关他的文献记载和遗存都少得不成比例。崇文门外这处唯一有文献可考的曹氏故居,因而被格外看重,但围绕旧居的确切地址,争议至今没有停息。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落成那天,张书才在新院子里走了走,感觉比他当年探访的那座民宅要小一些。院子按照清朝的格局恢复成三进院,布局成五间展厅和一间活动空间,正在举办“归籍京师”“寻梦蒜市口”“红楼一梦”等与曹雪芹有关的展览。
40年间得而复失,拆除又重建。现在,这处移址复建的新院落,与曹雪芹有怎样的关系?
1728年,仓皇入京
雍正六年夏天,少年曹雪芹跟着奶奶从江宁(今南京)回到北京。他们沿大运河而上,在通县的张家湾码头下船。从此,他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纨绔岁月。这是曹雪芹第一次来到北京。
曹家在张家湾原本还有一些当铺、田产、染坊等资产,不过此时已经都被罚没,一家老小无处容身。江宁织造隋赫德可怜曹家“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向雍正帝奏明后,从罚没的财产中,将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院子还给了他们,附带家仆三对。
变故发生在半年以前。雍正五年十二月(1728年1月),曹雪芹叔父、江宁织造曹頫因骚扰驿站、亏空帑项和转移财务的罪名被革职获罪。曹家在京城和江苏两地的家产、人口全部被罚没,赏给了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显赫将近六十年的望族曹家,至此家道中落。
曹頫之父曹寅,幼年时是康熙皇帝的伴读,曹寅之母是康熙的奶妈。因为这一层渊源,康熙帝对曹家两代人感情深厚。后来,曹寅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既是肥缺,也是能够直接与皇帝通信的耳目,深受器重。最显赫的时候,曹寅还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同为“江南三织造”之一的苏州织造李煦,则是曹寅的内兄。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江宁织造府。曹寅去世之后,曹頫继任父亲的职位,然而等到纪律严明的雍正登基,他对曹家的感情远远不如康熙,经济亏空事发,曹家没落。
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元妃省亲的煊赫、查抄荣国府的惊惶,或许都有曹家的影子。
居住在蒜市口十七间半期间,曹雪芹开始在京内谋职。他与姑姑家——平郡王府(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内)走动频繁,当时曹雪芹的表兄平郡王福彭正深受恩宠。红学家胡文彬曾提出,平郡王府的家史和福彭的事迹,作为素材融进了《红楼梦》之中,故事里风度翩翩的少年北静王,就有福彭的影子。曹雪芹还进入专收旗人子弟的右翼宗学(位于西单石虎胡同)任职,在此结识了终生好友敦敏、敦诚兄弟二人,后者留下的诗句,往后成为研究曹雪芹的重要资料。
后来,曹雪芹移居西山荒僻的黄叶村。某年除夕,他在腊月寒冬过世,不到五十岁,籍籍无名。他在京内的旧居到底在何处?很多年间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
1982年,故居重现
1982年,张书才已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了10年。冯其庸等红学研究者时常来馆里查找与曹氏一族有关的档案,耳濡目染间,张书才也对红学略知一二。那些年正值红学研究热,庚辰本的《红楼梦》定本正在整理中。有一天,他在馆中查找清代内务府档案,无意间发现了一份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记载了曹寅之妻回京后落脚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的事。这份500来字的档案,开启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红学热门话题。
张书才找来一份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在崇文门外很容易就找到了蒜市口街。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长约二百米。从图上能清晰地看出来,蒜市口街路南的院落都很空旷,应该是车马客栈或店铺之类;而路北中间的四个院落,是布局规整的二进或三进院。他初步推断,曹家旧宅可能就是这四个院子中的一个。
“纸上考古”告一段落,张书才来到崇文门外实地踏勘。蒜市口的名字已经作古,这里现在叫做广渠门内大街。他自西而东依次看了路北的各个院落,其中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即地图中的蒜市口16号院)原为马家私宅,据马家后人马允升说是嘉道年间买下的,已有一百七八十年。张书才看到,门道中靠墙立着四扇高大的屏门,门板中间各有一字,合起来是“端方正直”——《红楼梦》里就有这四个字。马允升说,中院堂屋原先还挂着“韫玉怀珠”的横匾。张书才猜想,贾宝玉和贾珠的名字也许与此有关。
然而,由于历次改建,马宅已经完全不是“十七间半”的格局。但院子的一个小角落引起了张书才的注意:后院西北角的院墙,有一段向院里凹进。在《京城全图》里,蒜市口街路北东数第三个院落恰恰也有这个特征。他在《京城全图》上数了数这间院子原本的房屋数:十八间。十八间房屋中是否有一间其实是半间呢?
经过一番考证和踏勘,张书才认为,蒜市口16号院应该就是曹雪芹故居。他也谨慎地留了余地:“至少要比其他几个院落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曹雪芹在蒜市口居住时,崇文门一带是热闹的中下层社会,每天,南来北往的商旅在这里举办市集庙会,车马客栈里总是人声喧哗,货郎小贩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声越过墙头,勾着墙里妇人小孩的心。穿过几条街就是天桥,杂耍的、卖艺的、唱大鼓和莲花落的就站在路边演出。如张书才所说,这里“是商贩农夫、游民乞丐、市井豪侠乃至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荟萃之区”。正是在这里,青年曹雪芹深入市井生活,也品尝到生活的甘苦。这对于他思想的成长和创作的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1年,张书才就提出在此处修复曹雪芹故居、建立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的想法。他设想,东边为“曹雪芹故居”,依照《京城全图》修复十七间半;故居西侧可以建一个“《红楼梦》资料研究中心”,供红学研究和交流使用。
谁料,纪念馆尚未落实,这处院子就被拆掉了。
1999年,拆于城建
1999年6月8日,龙潭公园龙吟阁,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北京市政协、中国红学会联合召开了一次曹雪芹故居遗址研讨会。红学会会长冯其庸抱病参会,在会上发了两次言。他说,红学界都认为,把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定为曹雪芹故居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他还说,广渠门内大街道路要拓宽,房屋要拆迁,“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件事办好,不失时机地重建曹雪芹故居。”
研讨会的消息公开后,这处旧居成了红学爱好者探访的热点,很多人不远千里,见它最后一面。由于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正好位于规划红线内,当时还未登记为文保单位。虽然很多声音要求保留,但一年以后,这处院子还是被拆除了。当时正值北京旧城改造高潮,赵萝蕤故居、粤东新馆等文物被拆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去留也曾受到关注。
2001年8月,两广路全线通车,此后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多次建言尽快复建曹雪芹故居。2002年,已经不存在的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被列为原崇文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两年后,曹雪芹故居纪念馆正式立项,但此后就无声无息了。
有人始终没忘记这件事。2007年,现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社法委副主任宋慰祖当选崇文区政协委员,时任民盟崇文区工委主委王金钟在政协任期届满时,他找来宋慰祖,交给了他一摞资料,对他说,要持续推进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的复建。这是宋慰祖第一次深入了解这个故居,此前他一直专注于环境保护、工业设计等行业。他猛然发现,这处已经不复存在的院子,与他从小居住的榄杆市旁的老宅只有半站地之遥。小时候他跟小伙伴经常跑到这个院子里,从大门口的水龙头接凉水喝。他还记得,大门前有五级台阶,门口立着长方形门墩,门道里靠着西墙立着四扇绿底的巨大屏风,写着“端方正直”四个字。“每扇屏都有近两米多高,六七十厘米宽,每一个字高度都在我头顶上”。
一份个人情感灌注到这项任务里。起初那几年,宋慰祖有点迷茫,大家都知道这事,政府也很关心,但就是没进展,他也不知道怎么推进,“特别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复建遇到了什么坎儿,我能知道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应怎么写提案建议。”数年间他每年都在写提案和建议,相关部门每年也答复他,但依然没有显著进展。
2010年,崇文区和东城区合并成新的东城区,合并之初诸事繁忙。好在2010年和2011年,曹雪芹故居复建连续两年写进东城区政府工作报告,他觉得放心了。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调研,他逐渐摸索出提案方向,针对复建环节中的症结写提案:一开始是调整用地规划的问题,后来是产权和资金问题。被划定的旧居复建地段,一部分产权属于新世界公司,旁边有新世界的K11项目,另一部分土地则通过招拍挂被卖给了另一家企业,复建故居的地块横跨在两家公司分别拥有产权的土地上,其中的调规工作又持续协调了数年。等到协商好了,地铁七号线又要在附近设站,复建地段成为了地铁站建设的料场和工地。
宋慰祖说,一座小小的院落,如果只作为一座建筑,就是盖房子,大家都认为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文物复建,涉及市区两级政府的规划、土地、交通、文物等多个部门以及企业,牵涉到政策、法规、资金、市政、基建等诸多问题。每五年政府换届,是他格外上心的时候,害怕一换届这事就被遗忘了。“中国处于发展高速期,一换届又有许多新事儿要干了。”他说。
到2016年,宋慰祖已经连续10年推动这件事。在北京市两会上,这位每年都带着十多份提案和建议上会的“提案大户”,至少有一份是关于曹雪芹故居复建与利用的。到了第十年,他有些疲了,每年依然在提案、在呼吁,但办复报告总是类似,“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提,可能大家永远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必须坚持,这是责任。”往后几年,他认真关注官方各类文化发展导向和政策——文化自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中轴线申遗、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让文物活起来、建设博物馆之城……将故居复建往上“蹭”,从各个角度阐述它的意义,喊出现在是复建这处故居的最佳机遇。
2019年依然是这样的一年。1月的北京市两会上,作为市政协委员的宋慰祖依然例行公事地为故居呼吁,但他心里觉得,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丝毫不知道,故居复建已经箭在弦上,上一年年底,地铁站终于封顶。
两会刚刚结束,他就接到东城区文旅局的电话,请他参加1月23日曹雪芹纪念馆复建奠基仪式。那天一大早,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中华立领的正装,外面套着一件精致的羊绒大衣,为纪念馆铲下了第一锹土。
2022年,旧居重生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像一个灰色的四方盒子,被摆在两栋高大写字楼的东侧,斜对面就是磁器口地铁站的一个出口。这里距离原址北移了60米、东移了100米,原址位于繁华的磁器口十字路口中心。
院子按照乾隆《京城全图》恢复了三进院格局,前两进院的五间房全部设为展厅,展示着故居的发现历史、红楼梦文化知识和曹氏家族的故事,以展板为主,辅以少许仿古家具等实物。院子不大,占地79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平方米,即使每个展厅都看得很仔细,半小时也就走完了。最后一进院的房屋关着门,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张长桌和一圈木椅,靠墙的书架上码着剧本杀的盒子。讲解员对观众说,这里将作为活动空间,会举办曹氏风筝制作体验、红学讲座之类的活动,“还有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剧本杀。”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采取社会化运营模式,产权归属于北京东城区文旅局,新世界集团下属的K11北京负责运营管理。纪念馆运营负责人、K11北京运营经理穆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纪念馆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希望借助学界的力量筹办红学大师讲座等活动。由于自负盈亏,纪念馆需要承担经营压力,所以最后一进院的“艺坊”将作为收费活动场所,一间小小的文创店也将开门营业。
“我们希望打造成贴合年轻人喜好的空间和网红打卡地,让展览更具互动性、体验感,而不是传统的故居纪念馆。”穆聪说,由于纪念馆的面积比较小,未来将与在旁边开业的K11 HACC艺术空间进行联动,“产生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今语境对话的效果”。
崭新的院落里,漆红的门窗和柱子锃亮得反光,檐下彩绘鲜艳。这座院落的建筑规格,较清朝时此地的普通民居偏高,装饰也更为奢华,似乎非此不足以表达后人对曹雪芹的敬仰。宋慰祖反倒觉得,如果大门恢复成黑漆色、窗户保持原木本色,会更符合旧时民居风貌。这处故居的独特之处,正是在宫廷文化之外,代表着北京平民文化和市井生活。
作为一处移址复建的历史文化建筑,其价值与意义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打量。2019年工程开工后,当年将这项任务交给宋慰祖的原民盟崇文区工委主委王金钟把宋叫到家里,跟他说,不要复建。“他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所用的也不是原始的材料,复建没有价值了。”宋慰祖说。当年故居拆除时,主要构件曾被保留下来,以备复建之用。但延迟多年终于动工时,这些构件都已经下落不明,包括“端方正直”四扇屏。宋慰祖对王金钟解释说,这里原本是唯一有文献证实的曹雪芹故居,有这样一个基地,我们才可以同世界文豪故居交流,促进各国间文化认同。

回到旧居本身,曹雪芹的故居到底是否就是那座被拆除的蒜市口16号院,并非没有争议。虽然20年前红学界权威们给出了一致同意的意见,但不同观点时有出现,近十年来越发增多。例如,2014年发表的《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再议》提出,蒜市口街并非只有200米长,可以向东西两边延展,这样就可以在沿街找到另外的十七间半院落。该文还提出,“十七间半”是产权概念,而非建筑概念,或许曹家拥有一个大院里的十七间半,而非拥有一个十七间半的独立院落。那么从地图中去搜寻正好有“十七间半”的院子,或许方向就是错的。
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蒜市口”“蒜市口街”“蒜市口地方”等概念分别涵盖什么区域,是否只能在那条200米的小街上寻找故居?张书才对各种观点了然于胸,至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么,蒜市口16号院就是曹雪芹故居的把握性到底有多少?40年后,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张书才没有给出百分之百笃定的回答,他依然觉得那个院子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当年拆掉地面建筑后,对地下留存的早期地基进行了考古。考古人员当时对张书才说过,中院建筑确实是清前期的。“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地基就能看出是十七间半,”张书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只说中院东房、北房和水井地基是清前期的。”
另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证据,就是当年马氏购房的房契。有一年,北京档案馆的一位朋友对张书才说,发现了马氏先祖购买蒜市口16号院的档案,并不像马氏后人说的那么早,而是同治年间,而且并不是从曹家手中购买的。到底是这间院子在曹家之后已经转手过,还是本不属于曹家,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用新材料于异地重建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现在唯一能够确证的是,曹雪芹确实曾居住这一带。两百多年前,那位一边在王府和官学谋职、一边构思着一个沧桑故事的青年,在此间留下过无数足迹。时至今日,这处雕梁画栋的崭新院落,已经不是往日旧物,而是一个以曹雪芹为主题的当代空间。当人们来此凭吊曹公,需要多一点想象力。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3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陈文韬】